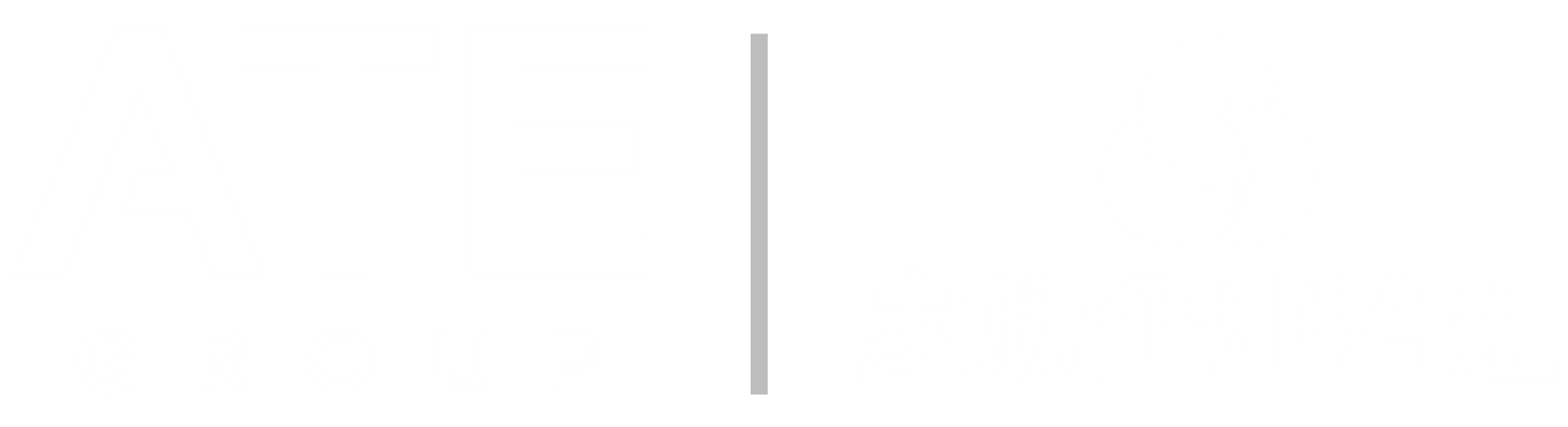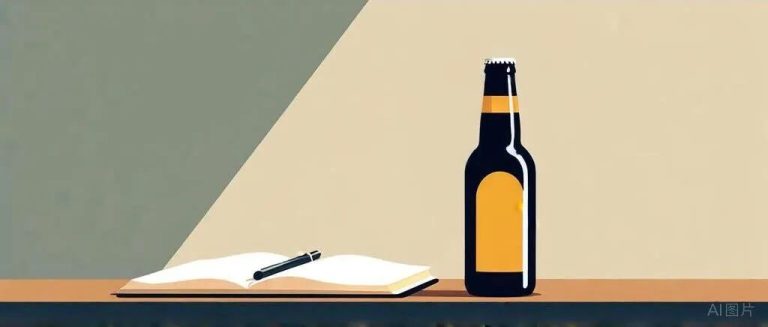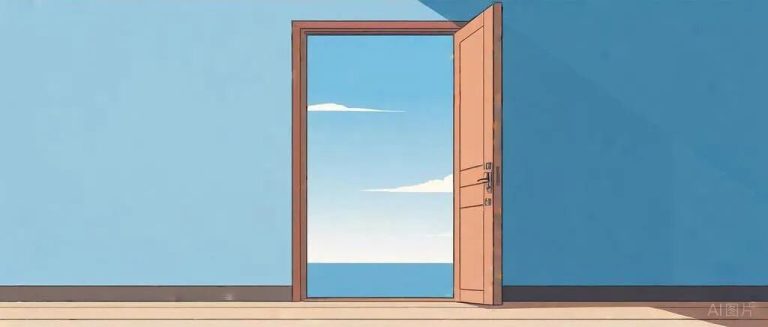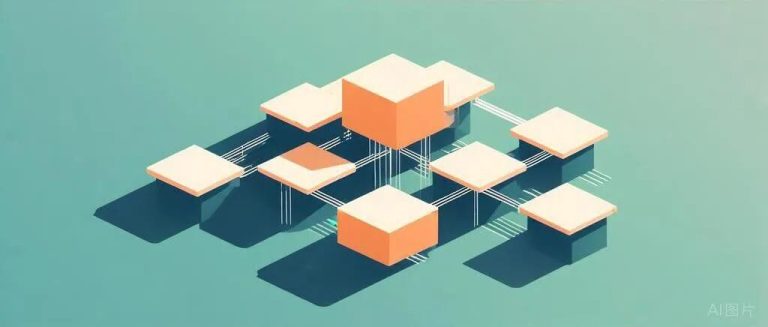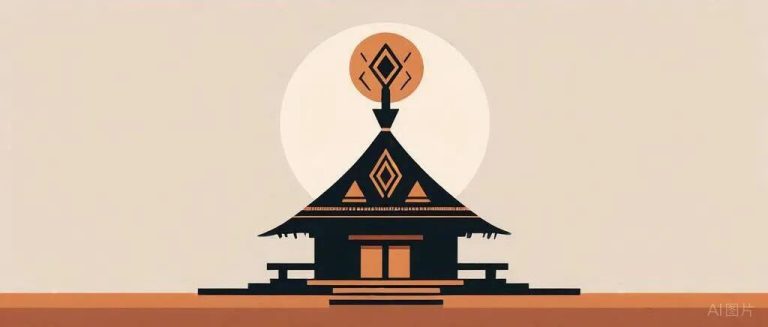“遗产纷争的背后,是家族人、财、业的多维危机”
“家族企业基业长青”是无数创业者的毕生期许。然而,近期娃哈哈背后的家族纷争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头部民营企业稳健传承的想象,也为所有家族企业敲响了警钟。纵观这场风暴,冲突的底层逻辑并非简单的遗产争夺,而是“人、财、业”三大核心失衡的集中爆发——家族成员认定与治理机制的缺位,家族财富规划与隔离机制的不足,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与权力制衡的紊乱。家族纷争的背后,是“人、财、业”的多维危机。
01 “人”的失衡:家族成员治理缺失带来系统性风险
娃哈哈家族成员认定与治理体系的缺位,直接引发了身份、权利、情感与形象多重失衡和公开化冲突。
家族成员身份界定模糊
- 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三名子女是否应被正式认定为家族成员?家族结构中是否还存在其他未公开成员?
- 杜建英作为三名争产子女的母亲、宗庆后前任妻子及娃哈哈创业期元老,却未被纳入家族治理的范畴。
家族成员权利与义务边界模糊
- 家族内部并未明确各成员对娃哈哈所有权、控制权等家族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继承人、治理人、管理人的角色责任混乱。控制权、治理权和经营权纠纷由此而起;
- 此外,对家族信息保密可能尚未被视为家族成员的重要义务,部分成员在争取个人权益时,将宗庆后的资产、信托等敏感细节公之于众,加剧了家族内部矛盾的公开化,直接损害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家族声誉及娃哈哈的品牌形象。
家族缺乏共同愿景与价值观,“家”的基础薄弱
宗氏家族的风波,其根源在于缺乏共同的家族愿景和价值观,使“家”失去了应有的温度与凝聚力。当血缘从亲情的底色变为权利博弈的筹码,家族终将陷入对抗和撕裂。如,宗庆后的亲弟弟、宗馥莉的亲叔叔宗泽后,在集团控制权之争中站在宗馥莉对立面,不仅公开表达对其管理方式的不满,还凭借自身持有的相关公司资源成为集团内部独立的利益力量,使原本可能通过家族内部协商解决的问题被进一步复杂化。
缺失身份规划,带来合规与安全风险
家族成员在进行重大个人规划时,必须将家族因素纳入整体考量,尤其是国籍等敏感领域,否则极易引发合规、治理和声誉等多重风险。宗庆后家族三名美籍子女的出现,直接打脸了其2013年“全家无外籍无绿卡”的公开表态。这一事实也迅速引发了舆论和监管层对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控制权变更等敏感问题的高度关注。
缺少内部争端处理机制,家族矛盾外化
继承冲突本应在家族内部解决,如今却通过媒体、法律公开对抗。随着宗氏家族的分歧走向公众视野,娃哈哈的继承、治理与重大战略安排已无法依靠家族内部共识解决——这不仅加剧了家族成员间的不信任,更动摇了家族企业的治理基础。
02 “财”的失衡:家族资产规划与分配机制存重大漏洞
家族财富定义不清、工具失序和法律冲突,使资产安全、继承效率和家族信任陷入多重危机。
家族财富范畴、权属分类模糊
对于境内外家族资产如信托资金(18亿美元汇丰账户)、企业股权(娃哈哈29.4%股权)、境外房产等财产,未做系统分类与清晰的权属明确,导致家族成员间对于“哪些属于家族、哪些属于个人”的分歧不断。
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未能有效匹配传承规划
- 娃哈哈所有权结构呈现“三角共治”。一方面,公司股权分散于国资、员工平台和家族三方之间(杭州国资委持股46%、宗庆后家族(由宗馥莉继承)29.4%、职工持股会24.6%)。另一方面,家族未设置任何现代治理工具或权利优化手段,以稳固家族主导权。因此,宗馥莉虽然名义上“接班”,却难以继承宗庆后的控制权,公司实际控制权被多方制衡;
- 此外,对娃哈哈的传承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实施。一是错失了资产“一致性持有”的战略窗口,宗庆后曾有机会收购国资股权实现彻底接班,但未就价格达成一致,致使控制权格局复杂化。二是未建立能够在家族实际持股分散时“拆分而不失控”的治理机制(家族持股平台、一致行动人协议等),导致企业的治理和运营在风险之下高度脆弱。
离岸财富信托工具被实际“击穿”
- 离岸信托的设立和运行过程中,缺乏基本的合规要素,包括未能提供正式的书面契约等文件,使该信托的法律效力受到质疑。目前香港高等法院已多次延迟裁决,要求证据补充。相关资产和权益的归属可能陷入长时间法律拉锯,将负面影响长期化;
- 信托账户21亿美元出现3亿美元缺口,且有110万美元已被宗馥莉转出,尽管受益人对资金用途和流向提出质疑,但信托机制已被实际“击穿”。
继承安排与遗嘱设计存在程序漏洞
- 宗馥莉提交的2020年遗嘱,见证人为高管、无家族成员或律师,程序合法性及内容权威性被质疑,影响了遗产分配的公信力;
- 原被动隐瞒的多子女家庭结构、信托安排在宗庆后去世后变成巨大风险点,遗嘱与实际家族关系严重不符。
03 “业”的失衡:顶层设计与权力交接的结构性紊乱
权力高度个人化、顶层控股布局落空以及权力交接真空,使娃哈哈的长期稳定和治理效率受到持续威胁。
顶层“三角共治”的所有权结构存在风险
- 以往有“强权”掩盖共治风险,问题未充分暴露。宗庆后在世时,凭借个人威望和集权管理,统领国资、职工、家族三方,未曾出现明显的治理障碍。但这种“家长式”强权下的三角结构并无法为企业传承和控制提供制度性保障,它所维持的稳态只是在创始人强力协调时、特殊环境下的“暂时平衡”;一旦遭遇权力缺位、继承变局或决策分裂,极易演化为治理僵局或外部资本觊觎的目标;
- “强权”关键变量变化,暴露结构性危机。宗庆后去世后,家族仅持有29.4%股权,职工持股会持股24.6%,而国资掌握46%黄金否决席位。由于国资和职工持股会各自利益和行为模式均可能左右大局,家族处于被动境地,尤其在杜建英现任职工持股会理事长时,这一结构成为公司权力争夺的关键变量;
- 诉讼进行时,三角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如果三名美籍子女继承诉讼获胜,将进一步分散宗庆后原本集中于宗馥莉名下的家族股权,“国资—职工会—多子女”格局会全面取代原有结构,三方彼此对立导致公司利益诉求分裂,内部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将长期失去平衡,企业极易陷入失控泥潭。
缺乏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导致内部权力分立且制衡机制失灵
- 娃哈哈的治理结构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威信,董事会与形式上的“三权分立”实际作用微弱。2024年宗馥莉“请辞—闪电复职”事件就是典型例证:事关集团控制权和相关公司主导权的纠纷,实际由国资、宗氏家族、资深管理层三方通过临时协商和口头协议推进,董事会及现代治理机制基本缺席,董事会无法成为利益冲突下的调节和稳定器;
- 公司治理及利益分配缺乏统一规划,内部力量分散,制度约束不足。如宗泽后虽未在娃哈哈担任管理职务,但其操控的其他相关公司与娃哈哈核心业务存在交集,可以对产业布局产生实质性影响,成为家族内部独立力量。
权力来源高度依赖身份认同,控制权基础脆弱
宗庆后去世后,宗馥莉的权威主要建立在“创始人之女”的身份认同之上,而非系统化、稳固的治理制度。在家族成员、部分管理层和其他股东眼中,这种单纯依赖家族血缘和“继承人”身份的权力来源,既缺乏广泛认同的基础,也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手段。这使得宗馥莉的实际控制权基础极为脆弱。2024年宗馥莉“请辞—闪电复职”事件即从本质上反映了娃哈哈内部各派力量博弈激烈、缺乏正式权力交接机制的现实。
无序权力交接,进一步降低公司治理效率
- 透明且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缺位,导致传承过程中公司内部权力变动剧烈。由于缺乏事先确定的高管继任或相关监督安排,宗庆后一去世,娃哈哈便出现大规模高管清洗。如,宗馥莉上任后,原集团元老吴建林等相继退出董事会,部分高管、老臣被大范围调整或“出局”,新的管理团队由宗馥莉及其信任的宏胜系高管全面接管。传承过程中的一切权力更替几乎完全依赖于家族成员的个人安排,而非有程序可循的公司治理框架。
- 此外,宗氏家族遗产相关的长期诉讼可能导致关键资产和表决权冻结,娃哈哈在3-5年内的重大决策效率将大幅受限,又进一步提升了后续公司治理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品牌形象与组织信任已严重受损
多方舆论战、“宫斗”情节、家族内部公开博弈,不仅动摇了娃哈哈企业文化的基石,还造成合作伙伴和市场对娃哈哈未来稳定的普遍担忧,可能严重影响娃哈哈的市场地位和发展前景。
04 结语:“宫斗”之外,唯有治理为根本
娃哈哈的“宫斗”充分揭示了家族企业在缺乏完善治理制度、财富管理工具、有效沟通机制、身份规划以及权力转移架构的情况下,可能遭遇的多维度系统性风险。这不仅是一个商业帝国的危机时刻,更是中国家族企业转型与传承过程中的长鸣警钟。
实现“家族企业基业长青”,实为一项系统工程。笔者在麦肯锡工作期间,曾参与2024年麦肯锡全球家族企业专项调研,通过比对全球1200多家上市企业的业绩表现及分析其传承路径选择,发现并总结出“顶尖家族企业能代代传承、业绩长青的‘4+5’成功范式”。其中,“卓越治理”被认为是最为核心的基石,其推动家族企业从“人治”走向“法治”、实现权责明晰、决策高效、防范内耗、并确保平稳传承的基础和保障。
“宫斗”之外,唯有治理为根本。